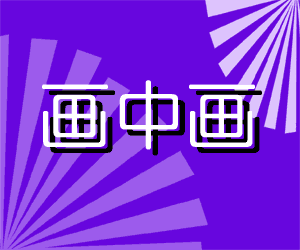余则成、翠萍原型并非一家人 解放后均继续从事保密工作
本期关注:“红色”特工
电视剧《潜伏》刚刚落下帷幕,剧中精彩的一幕幕扣人心弦。余则成的淡定,翠萍的坚韧将那些无名的地下英雄的故事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而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一批在隐蔽战线上默默奉献的英雄。日前,记者找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平西情报站工作的战士及他们的家属,了解到并非同一家庭的真实的翠萍和余则成的谍战故事。
事件回放
4月13日上午,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展馆在门头沟妙峰山正式开馆。展馆设在妙峰山涧沟村,这是当年平西情报站的电台所在地,也是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一个安放地点。据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电影《地下尖兵》和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潜伏》中的许多情节,都曾在这里上演。
前海淀文史办主任、研究平西情报史的张源洪介绍说,妙峰山地处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前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妙峰山分站就秘密隐藏在涧沟村。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保障,而该地区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当地群众不仅能保守组织秘密,还为交通联络提供了许多秘密工作人员。在战争年代,秘密电波、情报从这里发送,物资从这里转运,大批爱国青年、革命志士和国际友人也是经这里往来于延安与敌占区之间的。
真实版“翠萍”:见面20天 假夫妻真结婚
90岁的任远老人当年曾负责平西情报站晋东北情报小组的工作,是这批红色特工中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当年在平西情报站确实有一个与翠萍经历相似的女游击队长。在《潜伏》中,余则成与翠萍在党的安排下假结婚,以避免敌人对余则成身份的怀疑。在平西情报站,也有这样一位女性,她叫王凤岐。
和翠萍一样,王凤岐曾是游击队长,枪法也很准,所以组织安排她从河北易县假装王文的妻子来到北平城,而此时的王文正在执行秘密发报工作。王凤歧的主要任务就是掩护王文。
中共中央晋察冀社会部部长、平西情报站创建人许建国的妻子方林告诉记者:“真实的翠萍可没闹那么多笑话!如果像电视中的角色一样,那要有多少个脑袋给她掉啊!王凤歧可是很聪明的女子!”
王凤岐虽然也不识字,但是记忆力很好,上级交待的任务一般只要重复几遍,她就能记住。“不用纸笔,情报的内容更为安全。”在王凤岐来北平之前,组织专门派她到晋察冀根据地作过培训,专门训练如何掩护自己并保护同志的安全。负责发报的王文是留学苏联的学生,专门学习过关于电台的知识。
一个是留苏学生,一个是农村妇女,尽管两人文化与生活方面差异很大,但是由于共同的信仰,两人还是走到了一起。他们考虑到假结婚很容易被敌人识破,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两人在见面20多天后秘密举行了婚礼,成为真正的两口子。
由于生活观念方面的差异,解放后两人也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但还是十分恩爱。王文早已去世,王凤歧现在生活在天津,已经90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由于家人不希望老人被打扰,她本人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
真实版“余则成”:偷情报抓出根据地内鬼
平西情报站副站长李才的经历和余则成很相似,他潜伏在国民党华北剿共委员会,专门负责整理情报。如今李才已辞世,他的儿子向记者讲述了父亲当年惊险的谍战故事。
李才执行潜伏任务初期,在北平城开了一个名为源通祥鑫的毛线店。李才利用这份工作认识了不少富太太,从她们那里渐渐掌握了她们先生的情况。他了解到天津的老汉奸们想在北平组织成立一个华北剿共委员会,专门收集关于共产党的情报,以讨好日本人。于是李才通过当时石家庄市长儿子的引荐,进入了剿共委员会,并专门负责整理委员会内的情报。他借此打听到了国民党内部的人员构成,并认识了一些重要人物。
一次,李才发现了一份从晋察冀根据地截获的情报,情报透露近日共产党将有派兵行动。这份情报十分重要,如被敌人发现,我党的损失将是巨大的。于是李才利用职务之便,将这份情报从整理的文件夹中撤了出来。“像这样重要的军事行动都是由晋察冀根据地部署的,根据地很可能出现了内鬼……”想到这儿,他马上向组织汇报,请他们仔细排查。一周后,李才将扣下的情报原封不动地塞回了文件夹。此时,根据地已经改变了行动计划,特务也被抓获。
■巧装扮两送电台进北平
在选定平西情报站的地址后,晋察冀根据地决定在北平城内建立几个小电台,由小电台将情报传输到西山内平西情报站的大电台上,再由大电台将情报直接传到延安。小电台的功率不能太大,否则容易被敌人发现。组织上决定由李才负责北平的电台工作。李才打算直接运送电台进城,于是找到了自己的战友刘致祥,两人一起配合,先后上演了两次运送电台的故事。
1946年9月的一天早晨,刘致祥穿着西装,手提装有电台的皮箱到了西直门的城门口。一个宪兵走了过来,声色俱厉,要开箱盘查。“箱子是我们科长亲自锁上的,我可打不开,只让我早上八点半以前送到市党部,不得有误。”刘致祥扮成为科长运送东西的科员,同时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蓝色硬壳、上面有国民党党旗的小本子往宪兵眼前一晃。此时隐蔽在附近的李才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假装与刘致祥偶遇。“嘿,你怎么在这儿啊!”李才大声问。“这不是要给科长送东西么,但是被他们给拦下了。”“什么,要给科长送东西啊,那你怎么还不赶快走啊!耽误了可不得了!”宪兵一看来搭话的人也穿了一身西服,衣服上还别有国民党的党徽,就开始忐忑不安了。
“你还不放,耽误了科长的东西,你就别想再在这儿干了!”李才一句话一下突破了敌人的心理防线,赶快放了行。
另一次,李才则利用他的人脉,联系到了老朋友敖朔鹏。敖朔鹏是中国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有权调用中航的汽车进出西直门而不用停车检查。李才将电台悄悄装上车,顺利地带进了北平城。
■小疏忽险些断送潜伏生涯
李才在北平城做地下潜伏工作,而他的妻子邹时曾在一段时期内做发报员。为工作方便,组织决定将他的夫人送进北平城。邹时身穿厚旗袍,脚踩绣花鞋,赶着小毛驴从涧沟村到西直门。到了城卡,被一个宪兵拦下,要检查身份,邹时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随手亮出自己的良民证。这名宪兵一看这身打扮必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太太,马上毕恭毕敬地侧身让路。
邹时骑着小毛驴刚往城里挪了几步,就被另一个宪兵叫住了。“不对啊!你是从涧沟村来的,怎么会拿着新的良民证?那里还没有换发新的良民证呢!怎么回事?和我们走一趟吧!”
他们将邹时送到温泉日本宪兵队,开始拷打,并逼问她进城的原因。她的儿子回忆说:“母亲曾说过在工作时一旦被抓,就要抱着必死的决心,不能透露任何内容。”被敌人严刑拷打了5天5夜后,邹时没有透露半个字。最后,趁敌人放松警惕,邹时跑向宪兵队挂在墙上的炸弹,准备拉导线和敌人同归于尽。但马上被敌人察觉,敌人赶快将她拽住,并绑了起来。这一行为强烈地震撼了日本宪兵队的河端伍长,他没有想到中国竟也有如此刚烈的女子。
此时,我党内部的工作人员通过附近的老百姓打听到了邹时的动向,他们发现敌人不再逼问她关于根据地的事情,态度也开始转好,于是组织决定让李才借夫妻身份打探情况。李才身穿呢子大衣,脚蹬大皮鞋,头戴瓜皮帽,一副富人模样,来到温泉日本宪兵队。面对被毒打的妻子,他大嚷大叫:“你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病啊!在家里呆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到处乱跑!结果被共产党抓起来了吧,这还不够,还在那边帮他们的伤员包扎伤口!你是不是被共产党洗脑了,还想假装共产党啊!”听了李才的破口大骂,邹时意识到了他话中的玄机。于是邹时赶紧顺着演下去,表示自己知道错了,不该受迷惑,并表示很想念家里人,想赶紧回家。
李才走后,邹时并没有被宪兵队放出来,但是敌人的疑虑已大大减弱。河端伍长一直很欣赏邹时的刚毅气质,决心好好培养她。他将自己的自行车借给邹时练习,于是,邹时开始在院子里练车。慢慢地她发现自己骑车时,院里的官兵并不注意。一次,她试探地将自行车骑出了院,但出去不远就马上回来了。院内的官兵并没把她的举动放在眼里。从那以后,邹时每天骑车出院,而且一天比一天远,最后,邹时终于在被关一个多月后,从温泉日本宪兵队骑自行车跑了出来,沿山路一直骑回了涧沟村根据地。
健在者口述:供出假名单除掉真叛徒
任远 (时任平西情报站晋东北情报小组负责人)
抗战之初,中央为了开展敌占区的情报联络工作,挑选了一批有条件从事敌区工作的干部,一共13人,我就是其中一位。
1944年10月17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我被日本人抓获了,被关到了河北省丰润县看守所内。两个鬼子不带武器来“慰问”我。两个鬼子中,有一个名叫宫下,他问我:“你的电台哪里去了?”我装糊涂:“不是被你们在战场上缴获了么?”
他走后,我分析肯定是一些被俘的同志已受到审问,但真实情况一般干部是不会知道的。我开始改变策略,与敌人假装合作。我向宫下说明,第一,地下工作者的名单,我只能记住一部分;第二,我不能保证名单中的人,日本人可以找到。
宫下听后兴奋的表情,让我断定组织内部的名单敌人并没有拿到。于是我写出了两份名单,一份有约15人,包括姓名、地址、代号和派出或建立关系,这一份里没有一个人是真实存在的。第二份涉及了十多个人,有真有假,但这些真的都是抗战之初负责情报工作,事后叛变投敌的。我假供后,住进了唐山一朋友家,但仍被特务秘密监视。1945年小年夜,我在村民的帮助下成功地逃了出来。
人生的价值,贵在奉献,无私的奉献是人生的最高思想境界。我很幸运,我能成为一名无名的战士。
战后生活:一批“余则成”继续潜伏
在解放后,平西情报站很多同志由于在潜伏期做出了卓越贡献,被党派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还有一批像余则成那样继续进行潜伏的,李才就是其中之一。解放后,他在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工作,长期往来于香港、澳门等地。
为方便工作,国家决定,在李才任职后,报纸、电视都不能刊登或播出与李才有关的画面或照片。李才的儿子说:“当年我父亲每次出差都要换一本新护照,而且每次的姓名、职务都是不同的,照片也不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掩护身份。”解放后,王凤歧在天津市公安局任职,虽没有继续潜伏,但也同样做着保密工作。
由于情报工作在进行中都是单线联系,一个情报员只和自己接触过的一个或几个人认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多次运动中,这些人由于无法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饱受着煎熬,有的甚至被当成军统特务受到不公平对待。但是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斗争岁月,已如烙印一般深深刻在他们心上,他们始终无悔。